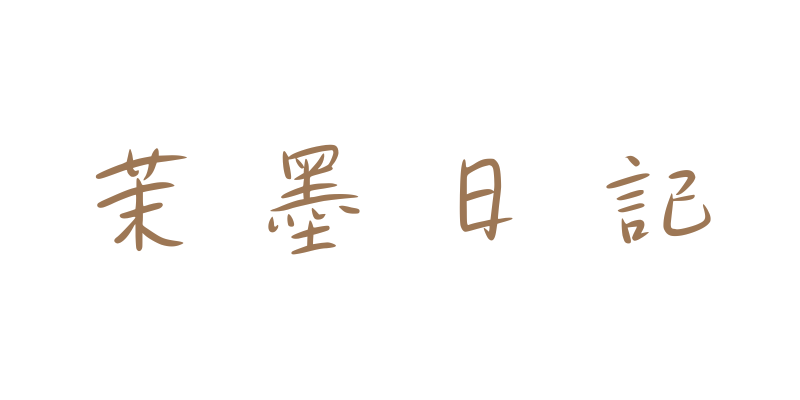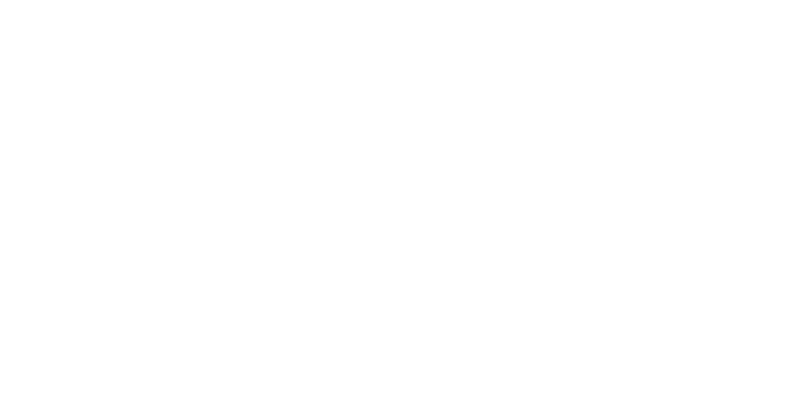我打給爸爸「哥哥說你們凌晨出發了,已經到美國了嗎?」,他淡定的說「對呀,跟媽媽在貴賓室吃東西了,哥哥確認過航班沒有因為山陀兒颱風取消,所以我們就照原定計畫飛。」,我回「好呀~到台灣再跟我說一下,我下周公司放四天雙十連假,我再回家一趟,一路平安。」
回家,是我三十多歲時才學會的新技能,也就是說,在我有所選擇的情況之下,我會選擇回家。
在花費很多力氣梳理、很長時間療癒以後,才明白父母也是帶著他們原生家庭的傷成為我們的父母,但他們的課題留給他們自身去處理,不讓自己淪為拯救其中一方的角色。成長過程帶給我的傷痕已然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心底的某一處,它就在那,不會消滅但也不具威脅。
療癒的過程,是在一次又一次自我覺察與情緒釋放中緩步前行的,是隨著自身生命歷程逐步往前推進的同時,學會以另一個角度和立場去看待過去綑綁自己的每個事件。是我強大了、心的面貌更成熟豐富了,是我超越傷痛了,不是我跟過去和解了。
最深刻的一次與爸爸一起站在他原生家庭的起點,是奶奶的喪禮。今年元旦是奶奶的頭七,喪禮期間村里的人天天輪流來陪伴我們守靈,可是,我完全認不得這些長輩,連怎麼稱呼都不知道。記得小時候過年期間,他們會來爺爺奶奶家坐坐,彼此短暫寒暄話家常,對他們的印象僅止於此,連續那麼多天碰上面,這倒是第一次。
可是,我總能從村裡長輩們的身上看到爸爸的特質,這個村裡的文化形塑爸爸的模樣,在冬日寒氣逼人的山裡,長輩們處處留意每個需要幫忙的地方,多做寡言、勤快熱心,不善言辭但是以行動表明良善的內心。那是一個資源不豐的村落,爺爺奶奶生長在一個貧困的年代,爸爸後來擁有的一切都是他和媽媽白手起家努力來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明白爸爸是怎麼成為這樣的他,他很少談起他的童年,我頂多只知道很瑣碎的片段。必須走過這一遭,我才更能夠接受我成長過程中別無選擇得經歷的每一個辛苦不安,是因為當時父母有他們現實條件上的限制,在我幼年時期,他們其實已經竭盡所能,抵擋著現實、承受著自身生命課題,邊站穩步伐、邊學習如何養育我。
我甚至可以推想,如果時間再往更早回溯,他們勢必也是在父執輩提供的成長環境裡經歷了無數個創傷,極有可能比我所經歷的加倍辛苦疼痛……果然,人的身上,刻有世代的傷痕,而我們得有意識的學習圓滿自身。
「妳不方便拿香沒關係,看要不要用手拜拜就好,等下我們過去那邊跟媽媽一起燒蓮花金給阿嬤。」
「爸爸,這個放進去爐子裡面就好嗎?」
「不可以隨便放,要接火。」
聽不懂,於是把摺得滿手的蓮花金遞給爸爸,先看他怎麼做。原來,接火的意思是等爐子裡的火焰沿著蓮花金摺疊拱起的小山脊燒到尾端的時候,再把手邊已對折整齊的蓮花金分次放入,接連著火焰往下延燒,爸爸一樣不會多說,我也一樣擅長自己看懂。
一疊又一疊的蓮花金,我邊燒邊在心裡跟阿嬤說「阿嬤,妳要在另一個世界學習把妳自己愛回來,為了我,也為妳自己。妳要捨得吃穿花用,過得幸福快樂。」喪禮後的過年,我跟爸媽飛回墨墨,只認真做三件事,吃飯、睡覺、曬太陽,然後無法控制時不時想阿嬤哭一下,也把握難得團聚的機會帶著爸媽跟哥哥一家一起旅遊幾個地方,休息一個月才返台復工。這場生命的終點,也是我看待許多關係的新起點,該斷捨離的,淡然捨去;該重新拾起的,加倍珍惜。
近幾年慢慢發覺回家變得比較容易,尤其是跟家間隔一片海洋的距離以後,回家未必是選項而是必須。除了我為自己打造的台北的家,要回哪個家都可以,回墨墨也好,回南部也行,或者飛往世界上任何一處,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是我想回也能回的家。
「幾點到? 媽媽去車站接妳回家。爸爸煮麻油雞等妳回來吃喔!」
「好~我周一去看健康檢查報告喔! 醫生說我交出一張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真的喔! 他說甚麼? 說妳特別健康嗎?」
「對~我現在身體狀況超健康,所以等一下我可以去逛夜市亂吃炸物,可以不用吃麻油雞~」
「最好是!」
「哈哈哈哈哈~」